《烟视媚行》是提灯夜赏韭菜花所著的一篇古代言情小说,这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阮令月没想到,她刚以妾室身份嫁进蒋家,蒋家就倒了。阮令月更没想到,这劳什子亲事,原本就是一场算计。蒋家只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人替嫡女上断头台,于是她没有退路,找上了那逮着人来抄家的容隽 ....
免费阅读
春风一顾乃是京中最大的花楼。
数栋楼宇临湖而建,连成一片。利用地势,大半都浮在湖上,白日里瞧着便是格外辉煌。楼中人从不辨具体时候,每至天色有些微变暗,便点起无数花灯,直将湖面照的一片旖旎灿烂。
阮令月将家中事物安排妥当,给那二人备好了饭食,又与许白交代了许多。出门前,她思虑过,可越想越觉得容府的人利用她还来不及,不可能会帮她的,便只找人去容府代她传了口信。
她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选把握最大的法子。
刚入未时,阮令月便在楼旁的茶馆中等着了,直至天色变暗,许多客人乘舟入了楼中,阮令月才起身。
方至岸边,撑船的小厮便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将她瞧了一遍。
这姑娘身上披着个极大的披风,帽沿将脸遮去了一半。
小厮瞧着那披风的料子属实不错,心道:莫不是哪家公子的妻室来寻衅闹事?否则哪有女子来春风一顾?
阮令月被人上下打量,却似浑然不觉,兀自上了小舟,抬手将帽沿轻轻支起,瞧他一眼,低声道:“撑船吧。”
那小厮弓腰乐呵道:“这位贵人,我自知身份低贱,却还是要劝您一句:莫踏足此地。有些事儿啊,一旦做出来了,便容不得反悔,可人总要想清楚了,给自己留几分退路才是。”
虽是话里有话,却也并不过分咄咄。
阮令月并未多说旁的,只递了一个腰牌给他。
小厮瞧见,先是惊了一惊。
这腰牌,是春风一顾的腰牌。
春风一顾上下无论等级类别,皆是相同样式的腰牌,可质地却是天差地别,一眼便能瞧出。像他这等撑船的小厮,不过木质。他见过最多的楼中姑娘,乃是流莺,可流莺们的腰牌,也不过是下等玛瑙。
而这姑娘腰牌的质地,却是盈绿润透的翡翠,明显并非是普通流莺,怕是要到玉燕、甚至金乌的等级了。
(私设,春风一顾的姑娘等级分为五等,由低至高分别为:流莺、铜雀、白鸶、玉燕、金乌。等级越高,在楼里身份越高,接触的贵人等级也越高。)
小厮连忙躬身,连头都不敢抬,更是不敢直视,只道:“烦请姑娘立好,小的要撑舟了。”
阮令月立在舟头,小舟轻晃着,往春风一顾去。
那浮在水面上的楼阁,因着繁盛的亮光,显得格外耀目。越是靠近,越能看清梁柱上艳丽的纹络和精致的雕刻。四处可见硕大的鱼鸟花灯,各色灯光将这原本就勾人的地方,照的更多了两分旖旎。
这般地方,能叫任何来客迷醉其间,可于阮令月而言,却似个漆黑又阴森的冷窟。
阮令月仰头,长舒了一口气,努力将心下的波澜抚平。
当再一次踏入熟悉的地方时,脚下木板还是那般咯吱作响,她忽然顿了顿脚步,轻提了一口气,挺直了脊背。
浑身的颓丧之气,一荡而空。
门廊附近身着各色衣裳的流莺们,皆用团扇遮面,只露出怪异的眼神打量着阮令月,却又不敢靠近,小心翼翼地绕开了,可又想着瞧热闹,不愿走远。
一个小厮瞧见了,生怕出了乱子,连忙过来,赔笑道:“贵人怕是来错了地方,我们这地界……”
那小厮正劝着,却见阮令月将斗篷取下,露出了精致的面目。
她着一身水红色衣裳,暗金线绣大朵芙蓉花镶边,无光时不过普通纹络,此刻在花灯下立时便熠熠生光。腰间被暗金线绣的团花紧簇在一处,腰肢显得越发不盈一握,其下头用红绳系着的春风一顾的翡翠腰牌。
裙摆轻动,说不出的气韵。
四周流莺们一见她的姿容和腰牌,但凡手揽恩客的,立时便走了。其余则围立在附近,远远地瞧着热闹,窃窃私语着。
“这可是前几日跑了的那个金乌?”
“正是,往日我是见过她的。”
“什么金乌,人家年纪未到,都还没□□,却是个将来的金乌。”
“没□□?那不是值得大价钱?”
“不然若是你这么个流莺跑了,你当秦阿姆为那般生气?”
“你们瞧瞧她的头饰,可不是寻常的,我瞧着金乌也未必能有吧!”
“说不准人家自己寻了富贵恩客呢!”
流莺们的话极露骨,且十分刺耳,说话间葱白的手指时不时指向阮令月,一双双眼睛盯着她,或自哀或嘲讽。
阮令月恍若未闻,兀自镇定地往楼梯边去。
边走,边撇了那小厮一眼,她背脊挺得笔直,伸手将斗篷递给他,“倒是有几日不见了,吉安。”
吉安连忙躬身,本想着跟阮令月说句话,可周围那么多双眼睛瞧着,他只好笑笑道:“是啊,令月姑娘。”
却是踏上台阶,刚到一处昏暗些的平台,吉安便连忙开了口。
“令月姑娘,您跑了便跑了,为何还要回来!”
阮令月原本正兀自踏着台阶,却忽然回头,微微一笑,“哦?”
“我知道秦阿姆派了人去祸害你的家人,可打都打了,经不能改变了。可您此时回来,岂不是叫你家人白挨了打?”吉安有些急了。
阮令月忽然蹙眉,下了台阶一步,垂首低声问道:“吉安,梦娘她在不在楼里?”
“我们都有好几日没见过梦娘了,秦阿姆她也一直是一副没见过梦娘的模样,可哪回楼里没了姑娘,秦阿姆还不都是那副模样?”吉安说话有些急,“趁着秦阿姆还没来,您赶紧从一楼出去,能走多远走多远。一楼现下客人正多着,没秦阿姆的令,不会有小厮妄动惊了客人的。”
吉安说着便要拉阮令月的广袖,却被阮令月躲了过去。
“不必了。”阮令月冷声道。
吉安抬头看着阮令月的眉目,“您莫不是还想着救梦娘呢?快清醒些吧!想想梦娘她宁可自己凶多吉少,为得是什么?”
阮令月垂眸看他,忽而一笑,道:“你不必为我担忧。”
吉安劝她不过,只得跟上继续劝。
却是刚上了二楼,便正遇见从拐角屋内出来的秦阿姆,两人面上皆是一惊。
秦阿姆体态略微丰腴,有些年纪,却是风韵不减,身姿举止处处优美。她唇上涂着暗红口脂,带着一惯的笑意,却是身后跟了两个大汉。
她远远地瞧见阮令月,虽是笑着,可目光中略微带了些诧异。
她身后两个大汉抬脚便要往前去抓阮令月,原也是她默许的,可走近了两步,却忽然瞧见了阮令月发髻上别致的头饰,又轻喝一声:“慢着,莫惊了客人!”
阮令月在看见她的那一刹那,几乎忍不住恨意,想要扑上去,掐死这个伤害阿京的人。
凭什么她家舅舅那般纯善之人,被打的浑身是血,还折了腿。可这笑里藏刀的罪人,却还能在此处安然无恙?
可她忍住了。
她强压住内心翻涌的恨意,她知道,要想达成此行的目的,今日非要过了秦阿姆这一关不可。
便缓步上前,低声道:“阿姆目光如炬。”
发髻上的攒金丝华胜在灯下越发耀眼。她今日特地戴上了从蒋家顺回来的头饰,繁复贵重又甚是惹眼,目的便在于此,叫秦阿姆以为她已经有了身份贵重的恩客。
秦阿姆细长的眉毛微蹙,凤眼也弯了弯,将眸中复杂的情绪隐去,瞧着周围姑娘们不时轻瞟过来目光,温声一句,“到屋内说罢。”
倒是秦阿姆先转了身,后头那两个大汉也跟上。
阮令月瞧着她的背影,眸中恨意几乎溢出,掌心隐隐起了些汗意,面上却仍是维持着镇定,“阿姆,有什么话不能在外头说的?”
秦阿姆在这楼里向来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儿,可阮令月不能跟她进屋。
若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,那便是悄悄消失了,也不会有人提起,大家只会装作不知情。阮令月丝毫不怀疑,秦阿姆也一向有这个令人恐惧的本事。
她不能冒这个险。
“哦?”秦阿姆微微回眸,面上仍是带着笑意,温声朝那两个大汉示意,“抓住她。”
廊边的花灯纷繁,将场面烘托得格外热闹盛大,然此刻,这廊上却是有些安静。
眼看大汉两步便到了阮令月身边,伸手便要抓人。忽有看热闹的姑娘见此情景,惊叫了一声,引得众人齐齐看了过来。
“谁敢放肆!”阮令月朝那扑来的二人低吼一声。
话是说给大汉听的,可她瞪了那二人一眼之后,却又眯了眼睛,看向秦阿姆。
那两个大汉也惊了,现下当真是瞩目的很,且他们看着阮令月脊背挺直,底气甚足,一时竟被骇得不知该作何反应。
阮令月几步到了秦阿姆身边,低声道:“阿姆,我头上这些珠玉钗环,皆是源自容府。若是阿姆不信,大可派人去查,我昨夜还伴在容家公子身边。”
她在赌,赌秦阿姆在三皇子倒台的当口,不敢招惹太子一派,不敢惹怒容隽。
秦阿姆终是转了身,一双凤眼瞧着阮令月,敛去笑意,定定地瞧着面前的姑娘,冷声道:“你的意思是,如今我动你不得?”
秦阿姆细细瞧着阮令月,她今日确是与同往日不一样了。
今日的她,目光仿佛格外有底气。
可从前的阮令月,便是在几个小金乌里头,都算是极乖顺的,每每与她接触,只觉她温软如蹲卧在窝中待哺的雏鸟一般。
如今,这是翅膀硬了。
不过,她是否真的出入容府,这可以查,如今她既已然现身,只要找人跟紧些,错处来日再罚也不是不可。
只是这个当口,她已经派人将她的舅舅打伤了,阮令月虽然暂时不知,可若再有旁的冲突,便极可能因着她将那位容大人得罪了,倒确实棘手得很。
秦阿姆在心里头暗叹:总还是要多些鞭子,小鬼儿们才肯好好干活啊。
复看向阮令月,“容大人既然已点了你的名儿,你此刻回楼里来做什么?”
阮令月也抬眸看向她,道:“蒙容大人偏爱,许我看望梦娘,可梦娘她不在家中。”
秦阿姆忽然笑了,看来她已经回过家了。
如此,那个傻子被打了的事情,她该是已经知道了。
秦阿姆微微摇头,温声答道:“梦娘她也不在楼里,且已经有几日没在了,我亦不知她在何处。不若你明日去求求那位容大人,替你寻人?”
阮令月蹙眉,心中的怒意越甚。
从秦阿姆的目光里,阮令月可以肯定,她知道梦娘的下落。
阮令月垂首,双手交叠朝秦阿姆躬身,将几乎要隐不住的情绪,掩在衣袖后头。
“谢阿姆告知,我去收拾些物件儿,今日戌时,还需得去容府一趟,劳烦阿姆安排打点。”阮令月低声。
“你如今也算是春风一顾的金乌了,择时候挑两个丫鬟吧。”秦阿姆笑道,看向阮令月身边的吉安,“吉安,你负责令月的车马安排。”
吉安立刻躬身道是。
秦阿姆吩咐完,面上带着一惯的笑意,转身时,却低声一句:“来人,将我身后这二人带下去。”
瞬时便有几个不知从何处来的小厮,将方才那两个打晕了大汉带走。
周围的姑娘们立时便开始了窃窃私语,多是震惊于向来说一不二的秦阿姆,今日竟是没将阮令月拿住。
阮令月眯了眯眼,究竟还是没忍住:“我家舅舅之事,可是阿姆所为?”
“是又如何?”秦阿姆微微侧首,忍不住蹙眉,瞥向身后的阮令月。
“来日方长。”阮令月看着她的背影,冷声道。
秦阿姆轻笑一声,缓步过廊上楼去。
吉安在一旁瞧了的一身冷汗,目送秦阿姆离开之后,才敢长舒一口气,低叹一声道:“我的亲娘祖奶奶哟……”
可当他回头看了看阮令月,也是满心满脸的惊恐。
这姑娘原来瞧着分明是个不大爱说话的软性子,竟不声不响同朝中新晋阁佬成了相好的。
今日还敢还跟秦阿姆叫板?
这金乌当真是比楼里旁的姑娘要厉害许多的,闷头办大事儿啊……
阮令月忽视周围人的目光和窃窃私语,只瞥了吉安一眼,挺直脊背,自顾往廊东侧走。
她今日来此要见的人,并非是秦阿姆。
行步间,她身上的首饰发出轻微有节奏的响动,听着极悦耳。周围花灯粉黄旖旎的灯光映在她身上,流光溢彩,纤软身躯显得光华逼人。
瞧见她行在廊上,二楼的铜雀姑娘们皆是装作不经意,眸子却又暗暗瞧着她,瞧着她的一举一动,试图模仿一二。
“令月姑娘,您往这边走做什么?”吉安不解,“那边住得可都是技艺师傅。”
“住口。”阮令月长眉微蹙,低声斥他,却是头也不回继续在廊上行着。
吉安连忙住了口。
在廊上拐了三回,才行至一处偏僻屋前。
阮令月驻足门前,听着里头正传来一阵琴声,弹的正是那曲醉渔唱晚。
她在门前静立了片刻,似是在欣赏这曲子。
吉安在一旁瞧着,忍不住一愣,心下满是不解:此时来寻这琴师作甚?
用琴音纾解情愫?
正疑惑着,却见她忽然轻提了一口气,将门推开,抬脚进去后又将门关上了。
把吉安留在门外。
室内琴音阵阵,檀香袅袅。弹琴之人技艺甚高,一声声将曲中人的醉态尽展。
阮令月绕过浅白色的屏风,往屋内轻轻行步。
室内正中有一张矮几,长琴置于其上,左侧香炉烟波袅袅。弹琴之人正坐在案几后头,闭目,神色投入,似浑然不觉阮令月已然入室,只自顾弹着。
阮令月直接跪坐在那人的案几前,给自己添了杯茶,等他弹毕。
他着一身石青色广袖衫,眉目如画中温润的佳公子,年纪甚轻,却是技艺娴熟,修长有力的手指,在琴弦上轻轻拨弄。
片刻后,一曲弹毕。
阮令月抬手替他添了杯茶,也不抬眸看他,只颔首行礼,恭敬地低声道:“亦琴先生。”
亦琴睁眼,瞧见阮令月,眸子里忽然带起笑意。
他自来是这般人,对任何人皆是带着温和的笑意,那笑自然到仿佛他本来的面目便是如此,且无半分谄媚讨好之意,直叫人觉得如沐春风。确是个与任何人都温善的。
可越是这等人,越是冷心冷情。
“令月姑娘,我记得你琴艺向来不错,今日可是有需我解惑的地方?”亦琴温声开口,声似四月暖风,敛袖伸手,执起阮令月递来的茶水轻抿了一口。
阮令月瞧着他温文尔雅面目,轻笑一声,不答反问道:“近些日子,想来先生很是困扰吧?”
亦琴伸手将茶杯轻轻置在案几上,笑意里带着几分不解,温和的目光直视阮令月,“令月姑娘何出此言?”
阮令月忽直视着亦琴的双眼,面上带了两分笑意。
“亦琴先生,那日我亲眼瞧见您摘了面具,吩咐秦阿姆杀人,您无需伪装了。”
亦琴面上笑意微滞,随后又笑开了,“原来那日之人竟是你,可惜错杀了翠文。”
分明与方才是同一张脸,可现下他面上带着的笑意,却忽然变了味道。
阮令月微微蹙眉,却听他继续开口。
“是啊,确是麻烦,三皇子一倒台,诸方势力蠢蠢欲动,有的想要将我春风一顾收入囊中,有的则是仇家,只想着将我将我春风一顾铲除了。”
亦琴忽而一顿,一双眸子定定地看着阮令月。
“你今日同我坦白此事,又提起三皇子,想必要说的话很是要紧。”
他伸手又执起案上那一杯茶,嘴边勾起一抹笑意,瞧着杯中微带波澜的茶水,“不过,若是你说出的话不能叫我满意,金乌还有许多,少你一个也无碍。”
这话倒是直截,阮令月原还以为他总要再装上一装的。
亦琴此人,从前因着儒雅俊逸的相貌,和看似温润的模样,骗得楼中大半姑娘的青睐。许多姑娘曾意欲勾 引与他,其中不乏玉燕、金乌,可他皆是以礼相待,一副正人君子模样,绝不逾越分毫。
这般气度的男子,在花楼里甚是少见。
想如此混乱不堪的地方,竟有一位谦谦君子,还是位造诣极高的琴师,自是绝无仅有。
便是阮令月初在他手底下学艺时,虽是年纪小,可见了他也还是忍不住心下小鹿乱撞。
直到前些日子,她亲眼瞧见亦琴摘了面具,吩咐秦阿姆将关在暗牢里不听话的姑娘处置了。
她才知道,原来这温和的琴师,竟是这般面目。
可那日亦琴察觉了有外人,所幸她藏的好,廊角的翠文却遭了秧,连辩白一句都来不及,便直接被他扭断了脖子。
那用来弹琴的有力长指,瞧着那般好看,却也是可以杀人的。
其实,细想想,依着他的模样和琴法造诣,断不必到这等腌臜地方谋生。
彼时她不懂那个显而易见的道理:事出反常,必有妖啊。
阮令月秀眉轻蹙,嘴角微勾,“看来秦阿姆也没想的那般忠诚,她竟还没告诉先生。我如今承容大人玉露之恩,片刻后还需得往容府去一趟。”
亦琴忽然眯了眼,笑意越甚。
“我可替先生在其中牵线引桥。”阮令月双手交叠,俯身朝亦琴行一礼。
“哦?”亦琴笑意微敛。
“只是不知梦娘现在何处?”阮令月抬眸细细看着亦琴的神色,试探道:“若在楼中,还请先生将她放了。”
亦琴忽然探身,一手撑在桌上,一手直接捏住阮令月的下巴,细细瞧着。
阮令月呼吸猛然一滞,脑海中不可抑制地想起那日被他扭断脖子的翠文。
亦琴瞧着面前这张脸,倒确实是有足够引人的资本。媚而不妖,性子也与寻常姑娘不同,竟还敢拿着此事同他谈条件。说容隽那般人会喜欢,倒也可信。
可此事于他自己而言,凡有不慎,不光身家,甚至要赔上性命,他自是要多思虑些。
比如她今日如此行为,是为着梦娘来的。若她为着梦娘,这般借势说谎,也不无可能。
总要试一试她在容隽跟前是否有分量才是。
他的手指因着多年弹琴习武,长而有力,将阮令月的下巴捏的生疼。
亦琴忽然低笑一声,方才的温润之感一荡而空,手下力道越发重,垂眸看着阮令月那双眼睛,“你胆子倒是不小,竟还敢跟我提条件。”
阮令月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骇得丝毫不敢动作。
可当对上他那双眼睛的时候,阮令月又忽然坚定了,道:“不光如此,我还想要秦阿姆的命。”
亦琴忽然将手松开,瞥了她一眼,轻笑一声。
刚斥了她谈条件,此刻竟还敢继续加条件,她当真如此有底气?如此倒是有几分可信了。
“这般瞧着,秦阿姆倒也忠诚,她并没告诉你梦娘如今正被拘在府衙大牢里。”亦琴低声一句,好整以暇地看着阮令月,浑没有方才的温润,反似个纨绔公子。
阮令月浑身禁不住微微一震,额间也升起了些汗意,“先生可知梦娘她为何身陷牢中?”
“两日前,她不知为何拿金簪,刺了一个衙差,便入了狱,大约是要被判死刑。”亦琴垂首,兀自抿了口茶。
阮令月忽然机警起来,只觉这信息来的过分简单。这话若非是诓骗她便是另有图谋?
果不其然。
“去求那位容大人吧。”亦琴轻笑出声,望向阮令月,“你说你于我有用,不过空口白牙,当真可笑。但若是你那位容大人肯替你救梦娘,我便信了你,有牵线的能力,事成之后,秦阿姆和那些不懂事的下人,随你处置。”
“可若是他不肯,你便要为你今日的话付出代价。”
阮令月此时心下一阵翻腾。
她今日会选择冒险来春风一顾,便是几乎肯定梦娘就是被困在春风一顾了。
借着容府威名,想着说不定能与梦娘见上一面,然后再想办法从中转圜。万万没想到,梦娘竟是在府衙牢里。
如此翻来覆去,几番下来,竟又到了容府。
可容府断没有道理去替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解决这些事情。然而她没办法,若亦琴所言为真,那么梦娘是真的杀了衙差,等闲救不了梦娘,眼下的情状,她只能去求容隽。
现下,倒是作茧自缚了。
阮令月瞧着亦琴,“如此,我从您这里能得到的好处却是少了许多,只得了个秦阿姆,我不大满意呢。”
亦琴将手上的杯子放下,“若是成了,你和梦娘便可直接脱离我春风一顾。”
“如此甚好,到时我与先生签字画押。”阮令月起身,朝亦琴躬身行礼,“时候不早了,我还需得去容府一趟,告辞。”
亦琴已然恢复了温润的模样,低声道:“告辞。”
却是转过屏风,出了门,阮令月忽然腿下一软,吉安连忙伸手将人扶着。
吉安一脸惊诧,看着阮令月额头冒起了一层细汗,面色发白,这模样分明是被吓的,连忙道:“令月姑娘,您是这楼里的金乌,他不过一个琴师,可需我教训他?”
阮令月回头瞧了瞧吉安,“你记住,这楼里你便是得罪了秦阿姆,也断断不可得罪此人。”
吉安不明白,却也没多说旁的,只搀着阮令月。
阮令月缓了片刻,低声问道:“往容府去的车马可备好了?”
“趁着您进去的空档,已经备好了。”吉安低声回道。
阮令月点了点头,长舒一口气,挺直了脊背,缓步往廊西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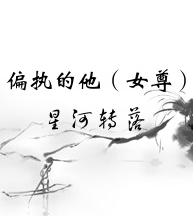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智能火网友
希望大家一直支持下去!
智能火网友
好看,加油啊
智能火网友
后面的队形跟上
智能火网友
居然有人! (๑ó﹏ò๑)
智能火网友
我是这篇小说的作者,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
智能火网友
谢谢qwq
智能火网友
给西裤打卡第四天! 小帅哥加油!
智能火网友
你玩不动了,为什么更文更的动
智能火网友
好看,快点更吧
智能火网友
终于等到了?